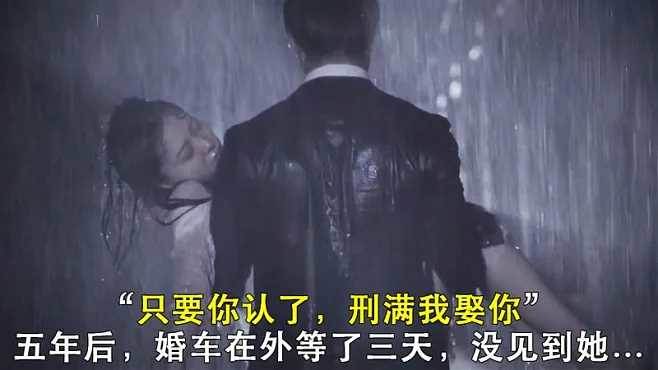《蝕骨危情》第324章
”
簡童臉色一白,“手機借我。”焦急說道。
拿到白煜行的手機,她立刻往薇薇安那里去電話:“我出國的事情,你要保密。這幾天,嘴守牢些。”話說到這里,薇薇安自然明白關于沈修瑾的一切,都不能夠說出去。
這才把手機還給了白煜行。
“他的腦袋怎麼?”難道腦袋也受傷了?
“阿修中槍后倒地,撞到了欄桿,腦袋上不是致命傷。”
“你能……讓我單獨陪他一會兒嗎?”
白煜行深深看了簡童一眼,默不作聲轉身離去,病房的門,“嘎達”一聲,闔上了。
病房里,悄無聲息,靜得讓人心慌。
她就站在病床前,靜靜地看著床上毫無聲息的人,悲傷幾乎罩住了整個的她,至此,依舊沒有淌下一滴眼淚。
干涸的眼眶,卻紅血絲遍布。
愛、恨、悲、痛,那樣的眼神,復雜得幾乎沒有人敢直視此刻的她。
一切靜悄悄,沒人看得透此刻她在想什麼。只剩下床畔的她,愛恨交纏,悲與傷交織,那樣復雜那樣無法用言語描述的,一眼也不眨地看著床上毫無生氣的男人。
===第二百六十九章 醒了===
白煜行和郗辰不知道簡童在這獨處的時間里,到底懷著怎樣的心情。
門再一次打開的時候,是沈修瑾的又一次的搶救。
走廊里倉促的腳步聲,每一次的搶救,眾人都提心吊膽。
簡童就像是被遺忘了一樣,所有人的心思,都在那個正在急救的男人身上。
沒有人說話,直到折騰到傍晚時候,醫生才宣布了危機暫時解除。
但這并沒有結束,在她抵達他身邊的五天五夜時間里,如這一次的瀕臨死亡的危機,一直籠罩在他的頭頂。
ADVERTISEMENT
五天五夜,十一次。
她數過,每一次搶救,便在心里數下一個數字。
她也不知道,她為什麼這麼做。
她甚至不知道,還有沒有力氣,繼續在心里,怨恨著他。
她連自己都搞不懂,又怎麼能夠弄明白沈修瑾。
那是一個清晨,有了一絲希望的清晨。
她守著他的病床邊,已經習慣了徹夜徹夜的盯著他失血消瘦的臉頰,靜靜看著,直到連她自己都扛不住的疲憊,依舊不敢深睡過去。
夜深的時候,她就那樣坐在他的病床前,看著那張熟悉得她一生也不會忘記的面龐,有時候她會看得著了魔,心里隱隱一個惡念——死掉她就自由了。
可每當她一想到,這人會死,會離開這世間的時候,心中翻滾的疼,幾乎讓她無法呼吸。
甚至是連她自己也不清楚,是盼著他活著,還是盼著他就這樣再也別醒過來。
“你就不盼著他醒來嗎?”白煜行咬牙切齒地問她。
她給不出答案來。
“他要是醒不過來了,你這里,就不會疼嗎!”白煜行激動地用手指,狠狠指著自己的左心房,質問一滴眼淚都沒有的女人。
會!會疼!幾乎不做他想,她的靈魂已經深切吶喊:會!會疼!很疼很疼!
“我以前嘗試過許多種痛。”她只是這樣說著,也不知道白煜行聽不聽得懂,也不管是說給白煜行聽的,還是說給她自己。
我以前嘗試過許多種痛,已經吃遍了許多種痛。你問我他醒不過來,會不會疼。會,會疼,但也就是疼了。反正疼著痛著的什麼的,早都已經麻木了。
對,麻木了。她心里一遍一遍對自己說。
ADVERTISEMENT
好像那樣就不會疼了,可她卻怎麼覺得這空氣凝重的缺氧的呼吸不暢:“我出去吹吹風。”
白煜行在她身后緊握著拳頭,他,無權責怪她,卻有怨恨她的冷漠無情。
可是如果她是冷漠無情,連續好幾個夜晚,她又一步不肯離的守在病床邊,守著那個病床上的人。
白煜行默默轉頭,看向病床上躺著的沈修瑾。
……
是夜
這是唯一一個她疲憊的睡過去的一個晚上。
那樣疲憊,趴在他的病床邊,就那麼睡了過去。
清晨的時候,她是被一陣嘈雜聲吵醒的。
睜開眼,床四周,圍滿了人。
她首先看到床對面的白煜行和郗辰,只是他倆臉上的表情很激動,似乎都在看著……她順著他們的目光,看向了病床上……猛地!
瞳孔驟然收縮!
她就那樣愣愣地張著嘴巴,傻乎乎地一眼也不眨一下地,看著病床上的那個男人,向著她眨著眼睛。
眨著眼睛???
驀然清醒了過來,腦子里的瞌睡蟲全部一下子跑光!
沈修瑾,醒了!
心里一下子彌漫了喜意,可她下一刻便意識到她內心無窮無盡的歡喜,一股自我厭惡漫上了心頭……為什麼為他歡喜?
又憑什麼為他歡喜?
她把這自我的厭惡,發泄到他的身上,變成語言,攻擊了過去:
“我沒有為你流一滴眼淚。我不會為你哭。”
當下,所有人猛地對她怒目相視,郗辰壓著怒氣喝道:“你過分吧!”
“阿修才剛醒,你就這樣刺激他的話?難道你真想要氣死他?”白煜行緊隨其后。
簡童話說完,就立即后悔了,卻不肯示弱,一句抱歉的話都不說,倔強地緊緊抿著嘴唇不語。
突然一道聲音:
“大姐姐,你很討厭我嗎?”一個大男人的聲音,卻委屈又難過,像個受了委屈的小孩兒。

 上一章
上一章
 下一章
下一章
 目录
目录
 分享
分享